
 2025社區十大人物
2025社區十大人物靈光集-43-《大風歌》

其實我壓根也不算會寫文章,嚴格來講,骨子裏面也是個泥腿子;所以不要指望我給你支持這個,支持那個。我所見,我所行,這一切就是我的世界,我只寫這些。
我一直認為,人就是一本書,人書之間,庭中一捧炬火,就燒穿了千年的夜。
我時常想,人這一生,究竟是在讀着書,還是在寫着書?石刻到竹簡絹帛,再到宣紙 A4 的文字,碑碣木牘凝固的嘆息,究竟是誰的故事,誰的春秋?大風一起就都吹走了,現在是電子時代。
高祖執炬而舞,大風自沛縣的原野上捲來,吹散咸陽宮的秦瓦,吹皺烏江的水波。他也未必,不,他肯定沒讀過萬卷書;亂世不容書生,碭山亡命徒,芒碭斬蛇人,他的老師是六國的驛道,是函谷的關隘,是鴻門的酒盞。每一程路都是一頁被血土浸透的紙,每一次敗逃都是批註。
天地為我師,大道披我身。這就是我理解的大風。
敗了不過死,成則千古之名。輕巧,卻重如泰山。藏着的是一個時代全部的重量。
翻開《史記》、翻開《國史大綱》,你能聞到那股塵土血腥混合的氣味。從陳勝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,到項羽火燒阿房宮三月飄煙,韓信胯下之辱。歷史從來不是温順的謄抄,是用劍鋒刻在骨上的銘文。所以史學家哪怕被閹了,也要寫到底,因為這是道德承諾,這是命。有的東西可死不可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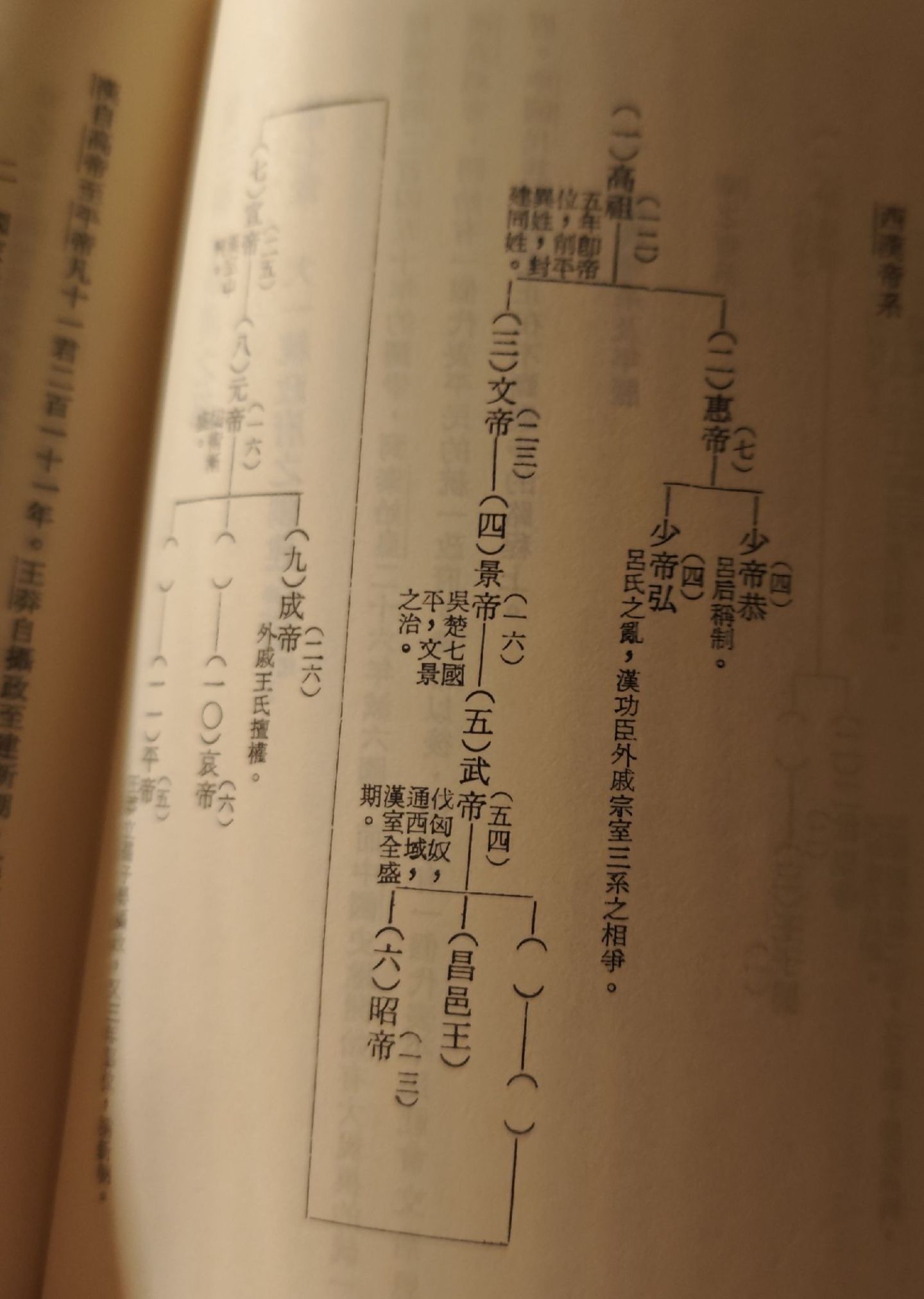
劉邦的路,是從亭長到皇帝的路。那路上有什麼?有鴻門宴,有白登山被圍七日的風雪,有未央宮建成時,蕭何説非壯麗無以重威。走過的每一里地,後來都成了大漢版圖的一筆;遇見的每一個人,後來都成了史書列傳的標題。
春秋的馬車載着孔子,從魯到齊,從衞到陳,從蔡到楚。十四年漂泊,七十二弟子跟隨,三千個故事在途中發芽。他沒有寫書,他把自己活成了書。一部《論語》,弟子們記下隻言片語,真正的《春秋》,是他走出來的那條路。那路上有子在川上曰的嘆息,有陳蔡絕糧的困頓,有吾道窮矣的悲愴。所以人的的一生,即是徘徊在舞台上的剪影。
書是什麼?是墨寫在簡上的字?不,是血淌在土裏的痕。人就是書。
炬火照亮的夜,高祖舞於炬下的那個夜晚,整個華夏都在看。
炬火照亮的不只是一個帝王、一個王朝,更是一個民族剛剛成型的輪廓。在此之前,中國是周天子的禮樂,是秦皇帝的律法;在此之後,中國有了另一種可能。一種來自草莽、來自泥土、來自最卑微者卻能容納最廣闊天地的可能。從不斷絕,從來就只因為一個容字。
《大風歌》,短短三句,二十三字:
“大風起兮雲飛揚” 成天地的氣象;
“威加海內兮歸故鄉” 立人間的功業;
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 提永恆的追問。
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而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這種焦慮讓漢朝成了一個開放的容器。張騫走出西域,司馬遷筆觸探入了夷狄,霍去病鐵騎踏過祁連。這個王朝不怕混雜,不懼異質,它在融合中尋找自己的形狀。
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當年拿破崙對亞歷山大大帝讚譽很深,就是説他去祭拜了阿蒙神,從此他的征服觸及了靈魂,他也因此征服了埃及。
銀漢是銀河的名字,也成了民族的名字。多麼奇妙的偶然,又是多麼必然的偶然。一個仰望星空的民族,用一個星羣的名字命名自己。從此,我們的血脈裏流淌着星光;換到西方,又迴歸了一,因為卡爾薩根也説,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裏面都藴含着星辰。
為何獨對劉邦有感?不是因為他是先祖。
李世民不好麼?貞觀之治,盛世華章。可他是關隴貴胄,是太原公子,他的起點在雲端。我們仰望他,如同仰望一座完美的雕塑。太完美了,完美得讓人難以親近;朱元璋不好麼?從乞丐到皇帝,真正的底層逆襲。可他手段太酷烈,胡惟庸案、藍玉案,血染金陵城。他自己恐懼太深,深到要用無數頭顱來填埋,這是懦夫所為。
唯有劉邦,泥腿子卻不失灑脱;帝王卻仍有市井的煙火氣。他會罵人,會逃命,會在功成名就後回沛縣和父老喝酒唱歌,會抱着戚夫人説 “為我楚舞,吾為若楚歌”。他的人性沒有被皇權完全異化,他的温度沒有被龍椅完全冷卻。
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,五十三年,五個朝代,十多個政權。皇帝如走馬燈般更換,今日黃袍加身,明日身首異處。可就在這混亂中,有一種別樣的生機在萌發,門閥徹底崩潰了,世家大族煙消雲散了,任何一個人,只要夠狠、夠能打、夠有機遇,都可能成為天子。
趙匡胤陳橋兵變,郭威、柴榮又一次重演。可這個武夫出身的皇帝杯酒釋兵權,用最温和的方式解決了武人干政的痼疾。為什麼?因為他懂得那些將軍們的心思,他曾經就是他們中的一員。我不評價那個人後半生所為,但就憑那一句 “從羣眾中來,從羣眾中去。” 絕對是人傑。泥腿子懂泥腿子,這是貴族永遠無法抵達的共情。
説了這麼多,不是説不要去讀書,反而是説書不是路,但書能告訴你路在何方。只是你不能拿着地圖,看着路標,就覺得自己知道天下,就不用去走路了。
司馬遷寫《史記》前,走遍了大半個中國。他上會稽,探禹穴,窺九疑,浮沅湘,北涉汶泗,講業齊魯之都。那些古蹟、那些傳説、那些還在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,都是他筆下的血肉。沒有這些行走,《史記》不過是又一部枯燥的編年。為什麼它是史家之絕唱?原因就在於:
欲知此事必躬行。
杜甫也是。他的詩為何被稱為詩史?因為他親眼見過 “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” 的開元天寶,親身經歷過 “國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 的安史之亂,親自走過 “飄飄何所似,天地一沙鷗” 的漂泊之路,親眼看過,民不聊生的夜有吏抓人。每一個字,都是腳步的回聲。書是別人的路,路是自己的書。
諸葛亮未出隆中而知三分天下,因為他讀了足夠多的書。那些書裏,有管仲治齊的方略,有樂毅伐齊的謀略,有孫吳用兵的策略。但他真正成為諸葛武侯,是在走出草廬之後。看着周瑜放赤壁的火、自己親歷益州的險、祁山的雪、五丈原的風。這些,是任何書上都學不到的。
大風起時,歷史是一條長河,我們都是河中的水。
但是!有些水成了浪,有些水成了沫,有些水沉入河底,有些水蒸騰為雲。劉邦是那個掀起巨浪的人,他的浪,改變了河的流向。故道大風起兮雲飛揚。
這風從何而來?從陳勝吳廣死國可乎的決絕中來,從項羽彼可取而代也的狂傲中來,從韓信多多益善的自信中來,從蕭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的遠見中來。這風是無數人的呼吸,是無數夢想的匯聚,劉邦只是恰好站在了風口。
但是那個執炬而舞的身影,從此定格在民族的記憶裏。出身可以卑微,學識可以淺薄,但只要敢走,只要不回頭,路就會在腳下延伸。敗了,不過是歸於塵土;成了,便是書寫歷史。
這不僅僅是劉邦的故事,這是每一箇中國人的潛在敍事。整天講自己贏,最後輸光光,這不是本事;人可以輸一輩子,但最後那一次一定要贏。
最後,回到那個字漢。銀漢的漢。
一個簡單的字,一個複雜的民族。像銀河一樣,由無數星辰組成,每一顆星都有自己的光,合在一起,便是璀璨的星河。
漢是劉邦建立的王朝,但漢也是共同的名字。它容納了楚辭的浪漫、秦法的嚴謹、齊學的博大、趙風的慷慨。張騫帶回了葡萄和胡琴,讓佛教傳入了中土,讓胡服騎射融入了華夏衣冠。
華夷之辨?不,漢從來不是封閉的城堡,而是開放的庭院。它有門檻,但門始終開着。它有自己的核心,卻不拒絕新鮮的血液。秦失其鹿,天下共逐之;誰要讓黃河長江之水倒流,那便不再是漢,乃真反賊也。
這才是真正的大風,不是摧毀一切的風暴,而是讓雲飛揚、讓鷹翱翔、讓種子遠播的風。它吹過兩千年,吹到今天的高天之風、高祖之風。漢絕不是也不能是從普魯士吹到西伯利亞的寒風。
合上手中的書,望向窗外的夜空。星河燦爛,哪一顆是沛公執的那炬火?哪一縷是高祖唱的那陣風?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,我還在走,路還在延伸,書還在寫。
每一個活着的人,都是一本尚未完成的書;每一步踏實的腳印,都是一行正在書寫的文字。
世界的風在吹動,時代在前進,那一天不會很慢到來,那一天馬上到來了。
大風起兮
且行,且歌。

本文版權歸屬原作者/機構所有。
當前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,與本平台立場無關。內容僅供投資者參考,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如對本平台提供的內容服務有任何疑問或建議,請聯絡我們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