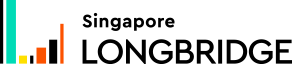2025社區十大人物
2025社區十大人物《踏月追星》

少年李漁蹲在北海的礁石上,手裏攥着漁網。鹹腥的風像時間的舌頭,舔舐他十二歲的臉龐。海水在暮色裏染成黛紫色,浪花咬着他的草鞋。
“捉到啦!” 他猛的提起漁網。銀鱗網中亂跳,定睛一看,哪裏是魚,竟是一面鏽跡斑斑的銅鏡,鏡面倒映着他變形的笑臉。
鏡子裏忽然漾開漣漪。他看見的不是自己,而是個駕龍的遊人,衣袂飄飄,正越過燃燒的羣山。遊人回眸時,眉間有一點硃砂痣,和他耳後的胎記一模一樣。
“喂!” 遠處母親的呼喚傳來。
李漁慌忙將鏡子塞進懷裏,冰涼的觸感貼着心口。那夜,他在油燈下擦拭銅鏡,鏡面逐漸清晰,映出三個重疊的影子:一個是此刻的他,一個是駕龍的遊人,還有一個醉卧雲端的歌者,正舉着酒葫蘆對月而飲。
“都是我?” 他喃喃自語,銅鏡突然燙得驚人,他手一鬆,鏡子墜地...碎了。
碎片化作千百隻螢火蟲,在他小小的卧房裏盤旋,拼成一行發光的字:
十萬八千夢,俱在此身中
然後光點消散,地上只剩尋常的陶片。窗外傳來更夫的梆子聲,已是子時。
李漁蹲下身,指尖觸到陶片邊緣時,忽然明白:剛才碎的不是鏡子,是他對我這個字的理解。有什麼東西松開了,像北海的泡沫終於捨得破裂,讓鹹風穿過空無的身體。
那是天啓元年,冬至。
十年後,李漁在長安太學讀書。他早已忘了銅鏡的事,只隱約記得童年某個夜晚,房間裏飛滿螢火蟲。如今他像所有求取功名的學子,在書卷與策論間尋找出路。
可長安城不讓他安寧。
每當晨鐘敲響,李漁便看見奇景:鐘聲如光刃,將青灰色的天幕劈開,晨曦傾瀉時,沒有刀劍揮舞,天空卻自然裂開金紅的傷口。他站在太學最高的藏書閣上,恍惚覺得自己是那抹光。他不是持劍者,而是劍本身。
“子非,又在發呆?” 同窗王煥拍他的肩。
李漁回頭,指着遠山:“你看,山有稜角嗎?”
王煥失笑:“山若無稜,何以為山?”
但李漁看見了別人看不見的。每塊山石都在化為塵埃,這個過程裏沒有吶喊,沒有抗爭,只有億萬年安靜的剝落。稜角不是山脊的固有屬性,只是時間雕刻時暫時的停留。
那天下午,兵部尚書來太學講演,主題是《少年當懷鋒芒》。老尚書慷慨激昂:“爾等當如新發於硎之劍,斬世間不平!”
李漁舉手:“請問尚書大人,晨光破夜,可需鋒芒?”
滿堂寂靜。老尚書眯眼看他:“你是李漁?李侍郎家的三子。”
“學生以為,真正的鋒芒不在對抗。” 李漁聽見自己的聲音陌生得像在轉述別人的話,“在於成為秩序本身,像光成為白晝,水成為河道海洋。”
他被罰抄《禮記》百遍。深夜燭火下,墨跡洇開時,他忽然想起童年那面鏡子。如果駕龍的遊人、醉唱的神仙都是他,那麼此刻抄書的學子,是不是也只是萬千化身之一?
窗外飄起雪。李漁研墨的手停頓,墨汁滴在宣紙上,慢慢暈成一個漩渦狀的圖案。他凝視着那個漩渦,忽然看見其中倒映出星羣移動的軌跡。不是此刻的星,是千百年後某個冬夜的星空。
“原來千百年這個概念,不過是浪花試圖記住自己的形狀。” 他輕聲自語。
抄到第九十九遍時,蠟燭燃盡。黑暗降臨的剎那,他看見書桌上所有的字都浮起來,在虛空裏重新排列,組成那夜螢火蟲拼出的句子:
十萬八千夢,俱在此身中
然後黑暗吞沒一切。他趴在桌上睡着,夢裏自己成了一場雨,落在貞觀元年的長安,落在開元盛世的長安,落在即將到來的安史之亂的長安。每一滴雨都沒有姓名,匯入護城河時,更忘了從哪裏來。
醒來時天已亮,雪停了。抄好的《禮記》整整齊齊疊在案頭,墨跡猶新。李漁走到院中,仰頭飲下一口雪水,涼意從喉間漫溯。
漫過胸膛,漫過頭頂。
他發現蒼穹從未在頭頂,一直在身體裏閃爍。
天寶二年,李漁進士及第,授官秘書省校書郎。同年,他在終南山下遇見雲遊道士清虛。
道人正在溪邊垂釣,魚竿無餌無鈎。李漁駐足觀看,只見道人閉目凝神,水面忽然躍起一尾赤鯉,在空中劃出弧線,竟化作一朵火燒雲,向九霄飛去。
“看見了嗎?” 清虛子睜眼,眸子清亮如孩童,“魚以為躍出水面就是自由,卻不知雲海才是更大的水域。”
李漁心中震動,想起十歲那年在北海的幻覺。他躬身:“請道長指點。”
清虛子領他上山。山路盤旋如迷宮,每轉一個彎,風景驟變:春櫻、夏荷、秋楓、冬雪,四季在一步之間流轉。李漁終於忍不住問:“道長,這路可有盡頭?”
“盡頭?” 清虛子笑指前方,“你且看。”
前方是懸崖,崖邊孤松上繫着一條褪色的紅綢。再往前便是萬丈深淵,雲海翻騰。
“跳下去。” 道人説。
李漁後退半步:“這?”
“你童年時不是碎過一面鏡子嗎?” 清虛子忽然道出秘密,“那時你就該明白。逆流的執着,順流時方知皆是同一條河。”
李漁如遭雷擊。他緩步走到崖邊,向下望去。雲海中,他看見無數倒影:駕龍的遊人正被龍帶入深淵;醉唱的神仙從雲端墜落;披星戴月的行人在峭壁攀爬。所有倒影都在下墜,可奇妙的是,他們的表情不是恐懼,而是釋然。
他閉上眼睛,縱身一躍。
風在耳邊呼嘯成古老的歌謠。下墜時沒有恐懼,只有一種奇特的熟悉感,彷彿回家。穿過雲層的剎那,他看見每一朵雲裏都藏着一個世界:有的世界正在戰爭,有的在歡慶豐收,有的剛誕生第一個嬰兒,有的正送別最後一個老人。
“原來雲海真是更大的水域。” 他在風中笑了。
沒有墜地的撞擊。他落在終南山另一側的山谷裏,清虛已在那裏煮茶。
“滋味如何?” 道人遞過茶盞。
李漁飲茶,茶湯裏有雪山的冷冽、岩漿的灼熱、初雨的清新、暮靄的沉厚。他放下茶盞:“道長,我還是不明白。如果一切經歷都是我,那麼選擇有何意義?遺憾又從何而生?”
清虛子指向山谷。時值深秋,滿山紅葉如血。一陣風吹過,幾片葉子提前飄落,在空中打旋。
“看見那片最早落的葉子了嗎?” 道人説,“它本可以在枝頭多待十日,看盡霜降後的銀裝素裹。但它選擇了此刻落下。不是風動,是它自己鬆開了葉柄。”
李漁凝視那片落葉。它在空中翻轉,陽光穿透葉脈,呈現出金色的脈絡,像某種古老的文字。
“遺憾不是缺憾,” 清虛子繼續道,“如山河在舒展筋骨時,自然形成皺褶。你且看這些山的褶皺。” 他拂開巖縫的枯草,“蓄着去歲的雨水,前年的落葉,百年前的種子。遺憾是時間的容器。”
當晚,李漁宿在道觀。夜半被歌聲驚醒,他循聲來到後山,見清虛子坐在崖邊對月而歌,歌詞古怪:
西天佛微笑,掌中一汪水。
倒映北冥魚,南荒龍擺尾。
東海歌者喉,披星行人累。
豔陽萬物唱,誰需要合誰?
歌聲在山谷迴盪,回聲從四面八方湧來,層層疊加,卻意外地和諧成天籟。李漁忽然懂了;沒有誰在合,每個聲音都是獨立的頻率,偏偏共振成了更大的樂章。
就像童年那面鏡子裏的萬千倒影,看似不同,實則同源。
他在月光下靜坐至天明。晨光再次劈開夜幕時,他低頭看自己的手。掌心紋路里,隱隱有星圖閃爍。那顆他總覺得摘不下的星星,此刻安靜地躺在生命線的起點,像初生時接引婆婆留下了一點温柔的涼。
安史之亂爆發,李漁三十七歲,任監察御史。長安陷落前夜,他奉命護送一批皇室典籍往蜀中。
馬車在官道上顛簸,裝書的木箱吱呀作響。行至馬嵬坡,忽聞前方兵變,只得改走小道。密林深處,叛軍追兵的火把如鬼火閃爍。
“大人,帶着書走不快!” 護衞焦急道。
李漁撫摸書箱。這些典籍裏有王羲之的真跡、司馬遷的手稿、屈原的殘卷,還有他年輕時在太學抄過的那些經書。每一卷都是文明的骨骼。
他閉目片刻,做出決定:“燒。”
護衞驚愕:“這可是..”
“文明的精髓不在紙上。” 李漁平靜地取出火摺子,“在人的記憶裏,在傳承的血脈中。”
火焰騰起時,奇景出現了。燃燒的竹簡上,墨跡沒有消失,反而浮到空中,在火光裏重組、舞蹈,化作無數發光的人形;有揮毫的書法家、吟詩的騷客、注經的學者、刻石的工匠。他們圍着火焰旋轉,然後向四面八方散去,融入夜色。
最後一卷被投入火堆時,李漁看見那是自己當年抄的《禮記》。墨跡浮起,組成的不再是經文,而是童年房間裏那行螢火蟲的字:
十萬八千夢,俱在此身中
然後光點匯入星羣。
追兵趕到時,只剩一地灰燼。首領惱怒地揪住李漁的衣領:“書呢?!”
李漁指向夜空:“在那裏。”
首領抬頭,看見銀河橫跨天際,忽然覺得每顆星都像文字的筆畫。他愣住片刻,鬆開手,嘟囔着 “瘋子”,帶兵離去。
護衞們已逃散。李漁獨自坐在灰燼旁,手觸到餘温尚存的泥土,忽然感到掌心一陣灼熱。他攤開手,看見掌紋在月光下流動起來,形成新的圖案。是敦煌的飛天,飄帶斷裂處,墨色最濃。
“傳説在熄滅前最亮。” 他想起清虛的話。
遠處長安方向火光沖天,那座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正在燃燒。李漁沒有悲傷,反而有一種奇異的平靜。他意識到,長安從來不只是磚石土木,是李白踏碎過的月光,是蘇軾未接住的問句,是所有在此活過、愛過、痛過的人共同做的、一場持續千年的夢。
夢會醒,但人類做夢的能力永在。
他站起身,繼續向西。背上沒有行囊,卻覺得揹着一口無形的井。裏頭沉着所有未完成的月亮,有玄宗未實現的盛世,楊貴妃未跳完的霓裳羽衣曲,李白未寫完的那首詩,還有他自己未寄出的那封信。
每一步顛簸,井水便晃盪成新的星空。
流亡第七年,李漁在成都郊外建了座草堂。他不再過問朝政,每日教書、種菊、記錄所見所聞。戰亂中,他遇到過很多人;失去一切的老樂師,在廢墟上彈奏無弦的琴;眼盲的畫師,用手指蘸墨畫他記憶中的長安;十五歲的學子,夢想重建焚燬的圖書館。
每個傍晚,李漁在草堂前給孩子們講故事。他不講聖賢經典,講那些破碎的傳説:
講敦煌的飛天,為什麼飄帶斷了反而更美;講殘荷如何用破了的葉面盛接雨水,倒映整個天空;講廣陵散絕響的剎那,那聲不肯散去的餘音,其實化作了後來所有古琴曲的魂。
“先生,” 一個叫阿阮的女孩問,“遺憾是不是很可怕?”
李漁看向遠山。暮色正從山脊滑落,像巨鳥收攏羽翼。他想起清虛的話,想起馬嵬坡的火焰,想起長安陷落前最後一夜,他在城樓上看見的萬家燈火。
“阿阮,你看過春草生長嗎?” 他問。
女孩點頭。
“春草漫過舊年足跡時,可曾理會那些足跡是喜是悲?它只是生長,新的風已經在醖釀另一場出發。” 李漁採擷下一朵野菊,別在女孩鬢邊,“遺憾不是行囊,是腳步本身。你踩下去的每個地方,都會長出新的故事。”
阿阮似懂非懂,但眼睛亮起來。
那一夜,李漁夢見自己回到北海。不是童年的北海,是千百年後的北海。礁石還在,但海岸線已改變。有個少年蹲在他當年蹲的位置,手裏拿着智能手機,屏幕上播放着駕龍游人的動畫。
少年抬頭,看見李漁,忽然説:“我好像夢見過你。”
“可能吧。” 李漁微笑。
“在夢裏,你跟我説..” 少年努力回憶,説:
十萬八千夢,俱在此身中。
李漁點頭。海浪湧來,泡沫在月光下碎裂,每一粒都映出不同的世界,他完全理解了。沒有誰來過,沒有誰記得。只有此刻,月光平等地照着空舟與滿舟,照着完整的與破碎的,照着記得的與遺忘的。
醒來時天已微亮。李漁披衣出門,見阿阮早早等在草堂外,手裏捧着一卷她自制的竹簡,用燒焦的竹片編成,上面用炭灰寫着歪扭的字:“我想去的地方...”
“先生,” 阿阮認真地説,“您説遺憾是腳步本身。那我想用腳步寫一本書,寫所有我去過和將要去的地方。”
李漁接過竹簡。炭灰的字在晨光裏閃爍,他彷彿看見這女孩的未來:她會成為遊歷四方的女史官,記錄戰亂後的重生;她會重建一座圖書館,比燒燬的那座更大;她會在暮年時,給她的孫輩講一個關於草堂先生的故事。
而那個故事裏,會有駕龍的遊人、醉唱的神仙、踏銀河的狂客,會有破碎的鏡子、無餌的魚鈎、焚書的火焰,會有所有遺憾與圓滿交織的、人間如夢的繁華。
“你會到達的。” 李漁將竹簡還給女孩。
早課的鐘聲從遠處寺院傳來。鐘聲裏,李漁聽見了清虛子的歌聲、長安的市井喧譁、馬嵬坡火焰的噼啪、北海浪花的嗚咽。所有聲音交織,沒有誰在合,自然成了生命的和聲。
他抬頭,看見晨光再次劈開夜幕。這一次,他不再問盡頭是什麼?因為他知道,用一生去交換的,從來不是某個具體的答案,而是交換這個過程本身。
躍過九霄的魚,不必知道雲海盡頭有什麼。躍起的那個姿態,已是全部意義。
寶應元年,叛亂平定。朝廷召李漁回長安復職,他上書婉拒,繼續留在了草堂。
晚年時,他變得沉默,大部分時間坐在窗前看山。學生們發現,先生的目光常常越過羣山,看向某個看不見的遠方。有人問他在看什麼,他只答:“看風在巖上寫字。”
臨終前夜,李漁將阿阮叫到榻前。當年的女孩已成中年婦人,是遠近聞名的史學家。
“先生還有什麼囑咐?” 阿阮握着他枯瘦的手。
李漁微笑,聲音輕得像要散入空氣:“你還記得小時候問的遺憾嗎?”
“記得。”
“我現在可以給你答案了。” 他眼神清明如少年,“遺憾是月光...照過李白,照過蘇軾,照過楊貴妃,照過安祿山,照過你我,照過所有活過與未活過的生命。它平等地照着,不問值不值得。”
阿阮淚流滿面。
“別哭。” 李漁抬手,拭去她的淚,“看窗外。”
月光正透過窗欞,在磚地上畫出菱形的光斑。光斑隨着雲層移動,緩慢掃過房間,照亮牆角的舊書箱、案頭的禿筆、樑上燕子廢棄的巢。
“空舟與滿舟..” 李漁喃喃,呼吸漸漸微弱。
阿阮以為他要説最後的教誨,俯身細聽。
卻聽見老人用盡最後的力氣,哼起一首沒有詞的歌謠。曲調古怪,像浪花拍岸,像風過鬆林,像火焰燃燒,像春草生長。
哼到某個轉折處,他停了。
阿阮等了很久,才發現先生已經離去。面容平靜,嘴角甚至帶着一絲笑意,彷彿剛看了一個有趣的把戲。
她按照遺願,將李漁葬在草堂後的山崗上,沒有立碑。幾年後,墳塋被野花覆蓋,分不清哪裏是墳,哪裏是山。
又一個十年,阿阮完成《山河紀》,在序言裏寫下這樣一段:
先生曾説,傳説在熄滅前最亮。而當他連熄滅的念頭也放下,傳説便化作了萬家燈火;每一盞裏,都有整個星空在安靜地旋轉。我走過很多地方,見過很多人。每個講述者都説,那些最美的故事,往往有未完成的結局、未説破的心意、未抵達的遠方。遺憾不是故事有缺陷,一切意外都讓故事有了生命。
就像此刻,我寫下這些文字時,窗外的月光正平等地照着我的筆墨、照着蜀中的羣山、照着千里外長安的廢墟與新築、照着北海的浪、照着每個正在做夢或將要醒來的人。
這便夠了...
書成那夜,阿阮夢見自己變成一場雨,落在貞觀元年的長安、落在開元盛世的長安、落在安史之亂後的長安、落在她從未到過的未來長安。每一滴雨都沒有姓名,匯入江河時更忘了來處。
醒來時雨真的在下。她推開窗,看見雨簾中,有個背影依稀像年輕的李漁,正踏着積水向遠山走去。每一步,腳下都漾開一圈漣漪,漣漪裏倒映着不同的星空。
背影轉過山坳,消失了。
阿阮沒有追尋,只是靜靜看着雨。雨聲裏,她忽然聽見所有時代的聲音:秦漢的夯歌、魏晉的清談、盛唐的詩吟、亂世的離哭、重建時的號子。層層疊疊,沒有誰在合,自然諧成了這片土地亙古的和聲。
她笑了,想起先生最後的話:
十萬八千夢...
雨漸漸停了。東方既白,新的一天正要開始。阿阮鋪開紙筆,開始書寫新的篇章。
晨光劈開雲層時,光芒從來不需要劈,夜與晝的交替,只是一場持續了億萬年的擁抱。
而她們所有人。駕龍的遊人、醉唱的神仙、踏銀河的狂客、抄書的學子、焚書的御史、教書的先生、寫史的女人。人類都在這場擁抱裏,找到了各自的位置。
不,不是找到。
是從來就在那裏。
就像星星不需要尋找夜空。
就像河流不需要尋找海洋。
就像每一個渴望不長大、卻又不得不長大的孩子,終於發現長大不是失去童年,而是童年化作血液,繼續在成年的身體裏奔流。
窗外,第一縷陽光正好照在草堂舊址。那裏的野菊開得正盛,金黃之花上,昨夜的雨珠還未乾。
每顆雨珠裏,都有一輪完整的太陽。
阿阮落筆,寫下全書最後一句話:
於是我們繼續前行,舟雖空,卻載滿了月光。

十萬八...
算了吧,道忘語。
本文版權歸屬原作者/機構所有。
當前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,與本平台立場無關。內容僅供投資者參考,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如對本平台提供的內容服務有任何疑問或建議,請聯絡我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