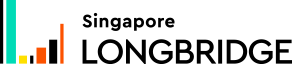2025社區十大人物
2025社區十大人物問史

歷史不是用來崇拜的,是用來還債的
這幾年,我越來越察覺一種奇怪的時代症候。
打開任何歷史論壇、視頻評論區,總能看到有人在為秦皇漢武的功過爭得面紅耳赤,為唐宗宋祖的排名列出一二三四,為明朝皇帝的業務能力寫萬字長文辯護,為清朝入關是不是中國正統吵到互相拉黑。他們表面上熟讀二十四史年表,其實不通曉歷代官制兵制,背不出每一個盛世的 GDP 數據,也不知道每一次變法的具體條款。
可是,這些熱鬧的爭論,總讓我想起本雅明的歷史天使。背對未來,面朝過去,被風暴吹着倒退飛進未來。翅膀已經張開了,眼睛卻始終望着廢墟堆積的地方。
問題不在於喜歡歷史。問題在於,我們似乎活在一個巨大的時間錯位裏。身體在二十一世紀,靈魂卻困在二十四朝的某一段,反覆打轉。
更麻煩的是,這種困常常以最驕傲的方式呈現。有人説自己夢迴大唐,有人以明粉、漢粉自居,有人認真論證如果穿越成某個皇帝會如何挽救國運。他們不是在欣賞歷史,是在認領遺產;不是在理解過去,只是在爭奪不存在的未來。
可我想問一句:認領的那份遺產,原主同意了嗎?
遺產的原主,不是李世民,不是朱元璋,不是任何一位雄主。而是那些一輩子沒吃過飽飯的佃農,是被徵發修長城死在路上的役夫,是在盛世賣兒鬻女的母親,是在明君治下依然活不過四十歲的黔首。
他們同意你把這份遺產認領成榮耀嗎?
歷史不是王位,不需要繼承。歷史是債務,需要償還。
我認識一羣人,他們把中國幾千年的興亡賬,一筆一筆寫了下來。
古代,錢、易、袁三位,有的寫,有的講。
從共工撞倒不周山,大禹治水,到家天下;從商鞅變法,有進無退,到秦二世而亡;從劉邦約法三章,到文景之治、漢武開疆;從桓靈賣官,黃巾起義,到諸葛亮南征,千年守土;從貞觀開元,到安史之亂,天街踏盡公卿骨;從岳飛天日昭昭,到崖山十萬軍民蹈海;從元末石人一隻眼,到明初《大誥》頒行;從揚州嘉定,到康乾盛世,再到鴉片戰爭、甲午、辛丑...
他們寫嬴政和劉徹,引用李賀的詩:劉徹茂陵多滯骨,嬴政梓棺費鮑魚。兩個求長生的帝王,一個埋在茂陵,一個爛在鮑魚裏。而他們寫諸葛亮,寫的是南中百姓千年後仍記得阿公,英軍入侵時發公告誓報守土之責。
他們沒有偏袒誰,也沒有放過誰。
盛世,天俾萬國,長安舉世瑰;盛世底下也埋着民怨,驕奢皇公,不聞民怨。名將,岳飛精忠報國,北方父老等了一百多年、等到崖山海戰都沒等到的眼淚。農民起義,蒼天已死,黃天當立,朱元璋從乞兒到帝王、最終讓《大誥》落滿灰塵的輪迴。
然後到了近代,另一位老人,丁教授寫過:
文夕大火,花園口決堤,螻蟻命微。香江有幸埋忠骨。民國,從三民走向墮落。
他們一路寫下來,沒有停下。
最後北師大的歷史檔案寫:“此出鄉關,孩兒立志,待學成方歸。三十二年,重歸故里,惟餘墳前碑。”;寫人民子弟兵,寫無名烈士,寫地震空降,寫洪水逆行,寫戍守邊關。寫主席萬歲、人民萬歲。
我對於這些評價並不完全贊同,有的人我從個人感情上討厭他,但我也不會否認他在歷史當中的定位。最重要的是:
歷史是一筆賬。把五千年來欠下的、忘掉的、被美化或被掩蓋的,一筆一筆,都記了下來。
合上賬本,債還沒還,還有路要走。
我們這代人,太習慣把歷史當成可以挑選的超市貨架了。
喜歡武功的就拿漢武開邊,喜歡文治的就拿仁宗盛治,喜歡硬氣的就拿不和親不納貢,喜歡風雅的就拿宋瓷宋詞。我們從中抽取自己需要的部分,拼成一個想象中的黃金時代,然後把那個時代當成精神故鄉,彷彿只要足夠虔誠,就能從故鄉借來一點榮光。
可是,那些時代裏的人,真的有資格拒絕嗎?
你穿越回開元天寶,長安城萬國來朝,酒肆胡姬如花,詩人才子如雲。可你是那個在坊市裏擺攤的小販,是要向宮市白交貨物的農夫,是被徵去守西域、十年不得歸的戍卒。你看到的是盛世,還是盛世的代價?
你穿越回洪武永樂,朱元璋殺貪官、復漢統,鄭和下西洋、萬邦來朝。可你是那個被編進匠籍、世代不得改行的工匠,是那個負擔三餉、顆粒無收的農民,是那個在靖難中被屠城的百姓。你看到的是復興,還是復興的成本?
人們總是站在帝王將相的位置想象歷史,卻很少站在那片土地上想一想:幾千年裏,這片土地上的絕大多數人,過的到底是什麼日子?
他們有盛世,賦税免了嗎?有明君,徭役停了嗎?有良相,賣兒鬻女的能贖回孩子嗎?有清官,被打斷腿的能等到公道嗎?
歷史書上的輕徭薄賦,是比上一個暴政輕了,不是不徵了。與民休息,是讓你喘口氣,不是讓你當家作主。
這些不是我的控訴,是事實;在當代,算是上層建築,在古代,是正統的漢皇后裔,流傳至今,有祖祠族譜為證。算是瘋了才開始講這些。最好奇的是,我都把這些當成恥辱,但是人們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光榮。
而承認這些事實,不是為了否定祖先,是為了對得起那些沒有留下名字的人。他們沒有祠堂,沒有諡號,沒有列傳,甚至沒有墓碑。他們是這條長河的河牀,水漲的時候被淹沒,水退的時候被遺忘。
我們現在還能站在岸上,説這條河偉大、壯闊、源遠流長。
可河牀説不了話。
後世理應把那些被盛世碾碎的名字,一個一個從土裏捧出來,擦乾淨,放回他們應該在的地方;而不是把二十四史當連續劇看,這一集姓劉,下一集姓李,再下一集姓趙,換主角、換片頭曲,底層的敍事邏輯從來沒變過。
梁啓超一百多年前就説過:中國人有朝代史的自覺,卻沒有中國史的自覺。
這話現在聽來,依然刺耳。
我們記熟了朝代表,卻很少追問:朝代更替的本質是什麼?是劉家換成李家,李家換成趙家,趙家換成朱家,朱家換成愛新覺羅。每一家都宣稱天命在身,每一家都説自己是萬民之主,每一家都在權力交接時流血千里。
這不是中國的全部歷史,但這是幾千年來反覆循環的那一部分。
為什麼循環?
因為家天下的邏輯從來沒有被真正打破。江山是皇帝的私產,百姓是私產上的附屬物。好皇帝是把私產管理得好一些,壞皇帝是把私產揮霍得徹底一些。但私產就是私產,不是公器,不屬於人民。
這個邏輯,才是封建最核心的遺產,承襲至今。
不是龍袍、玉璽、三宮六院,不是跪拜、避諱、株連九族,是那一句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濱,莫非王臣。是所有人理所當然地認為權力可以私有,江山可以繼承,人民只是臣民。
以為封建已經入土了?
可是我每次看到有人認真討論如果我是崇禎該怎麼挽救大明,每次看到穿越成亡國之君的話題下動輒幾百條策略,每次看到把某個朝代奉為精神祖國、容不得半點批評,我都會想:
那把龍椅,還沒燒乾淨。
我信興亡有數,但我真正信的是另一句。
李賀諷刺秦皇漢武求長生,梓棺茂陵荒廢;也寫成都武侯祠,千年松柏,香火不絕。
他不是説諸葛亮比帝王偉大。他是説,人民記得什麼,不記得什麼,自有道理。
秦皇漢武開疆拓土,功業赫赫。可老百姓去武侯祠燒香,不是因為諸葛亮六出祁山、北伐中原,是因為他治下南中不留兵,不運糧,是因為他帶去的技術讓當地人學會了耕種織布,是因為他死了之後,那片土地的人世世代代叫他阿公。
英軍入侵的時候,西南少數民族發公告:誓報守土之責。
一千八百年了,他們還記得。
我認為這才是歷史的重量。不是帝王加冕時的冠冕,而是百姓心裏那桿秤。
漢武帝的罪己詔,唐玄宗的馬嵬坡,崇禎的煤山。誰把人民當人,人民就記住他;誰把人民當耗材,歷史就把他當耗材,不是不報,時候未到。
所以,歷史不是用來崇拜的。
崇拜是把自己放低,匍匐在某座神像面前,祈求庇護、恩賜、榮光。可歷史不是神像,是無數具骸骨鋪成的路。匍匐下去,臉貼着的不是金身,是土。
歷史是用來還債的。
還什麼債?還那些被盛世碾碎的、被王旗遺忘的、被大歷史一筆帶過的具體的命。
還大禹治水十三年過家門不入、後來卻被供奉成神像的那個凡人,他本來也是人。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、出師表寫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,報的不是一家一姓,是他看見的那個天下。
不然呢?天下給曹操們嗎,殺的泗水為之斷流,還要寫首詩傷春悲秋,孽就是他們造的。
每一個戰亂裏餓死的孩子、每一個苛政下倒斃的老人、每一個被徵發就再沒回來的丈夫、每一個等着等着頭髮都白了的妻子。
他們不是數字,是人。他們沒有活成盛世裏的風景,他們就是盛世的地基。
我們現在站在這片土地上,説它遼闊、富饒、偉大。可地基不會説話。
那就由我們還能説話的來替他們説。
五千年的興亡賬一筆一筆寫下來,不是為了清算,是為了記住。記住那些不該被忘記的人,記住那些不該被粉飾的事,記住這條路是怎麼一步一步走過來的。
然後抬起頭,繼續往前走。
我不是某粉,不會穿越幻想裏的帝王將相,我也不是隻會憤怒的批判者。我是一個還債的人,站在歷史的出口,面朝大海。
前幾年,有人問我:你覺得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是什麼?
我想了很久,説:可能是現在,理應是未來。
不是因為現在完美無缺,遠未如此。是因為這是幾千年裏,第一次有人在權力和人民之間,説出了那一句人民萬歲;無論做不做得到,但是這句話出來了,可能最後他們也會浮沉,但是後來者説不定就能在這句話的基礎上面做的更好了。
不止是口號,是整部歷史的分水嶺。在此之前,江山是私產,人民是臣民;在此之後,至少道理上,江山是公器,人民不是主人也是人。
道理還沒完全變成現實,路還很長。但分水嶺就是分水嶺,過了那道嶺,水不會再流回去。
我們這代人的任務,不是往回跑,不是認領某段王權的遺產,不是替哪個朝代爭正統。
是把那條路繼續往前修。修到每一個人的尊嚴都被看見,修到人民萬歲從道理變成現實,修到幾千年欠下的債,一筆一筆還清。
那麼多帝王將相、金戈鐵馬、詩與骨、血與火,最後的篇幅留給一句話。
現在不是歷史的終點,是歷史的轉折。是我們終於知道,江山不是誰的私產,是所有人的家。
歷史不是用來崇拜的,是用來還債的。
債沒還完,路還要走。
那就走吧。

後記:
不知道為什麼,我看見人們,本質上還是在那把沒燒乾淨的龍椅前面排隊,都覺得自己能夠坐上去,都認為龍椅理應存在。
他們排着隊,心裏想的是:輪到我坐上去的時候,我一定坐得比上一個穩。他們不懷疑這把椅子該不該存在,只懷疑坐過的人沒坐好。
很多打着馬主義旗號的人,説自己是在反抗不公、嚮往偉大。其實他們只是換了一身衣服,重新跪回了原來的位置。只不過從前跪的是龍椅上的那個人,現在跪的是龍椅本身。
跪久了,龍椅就不是木頭了,是理。
討論不是要不要皇帝,是哪個皇帝更好。爭論不是江山能不能私有,是誰更有資格繼承。人們爭得面紅耳赤,其實共享同一個前提:這把椅子是天經地義的。
唯一的問題是:憑什麼覺得,坐上去就不是下一個消耗品?
龍椅從來不是座位,是祭壇。坐上去的人以為自己是祭司,其實第一刀祭的就是他自己。然後是土地,然後是糧食,然後是那些連名字都沒留下的人。
一輪燒完,換一個人,再燒一輪。
燒了幾千年,椅子還在,灰燼裏卻找不出幾根完整的骨頭。
有人説這是冷漠,説我不愛國。真正把這片土地當家的人,不會敢隨便認領它的王座。愛不是繼承榮耀,是償還債務。 這片土地太重了,不能在史書裏挑肥揀瘦,重到必須連那些被抹去的、被碾碎的、被美化成代價的命,一併扛起來。
所以走。
不是逃跑,只是去找那條能真正走出循環的路。
這條路在哪?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它不在那把椅子底下,不在排隊的人羣裏,不在任何一個宣稱天命在我的人口中。
它應該在別處。
不再需要神像的人中間。不跪的人中間。把人還給人、把世界還給人們的、緩慢而笨拙的努力。
龍椅還沒燒乾淨。還有人在上面找座位,還有人把江山當私產來懷念,還有人對着帝王將相的牌位磕頭,以為磕得夠響,就能分到一點餘暉。
從來如此,便對嗎?
本文版權歸屬原作者/機構所有。
當前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,與本平台立場無關。內容僅供投資者參考,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如對本平台提供的內容服務有任何疑問或建議,請聯絡我們。